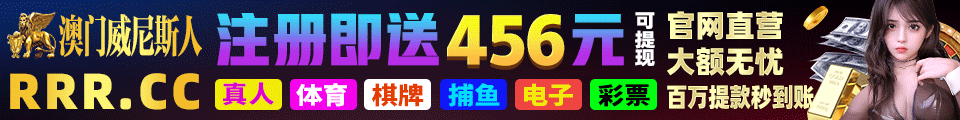网站名称 网址:55sm.xyz保存网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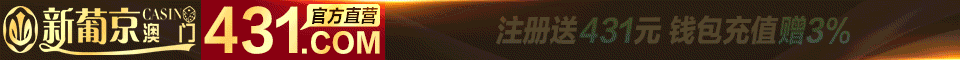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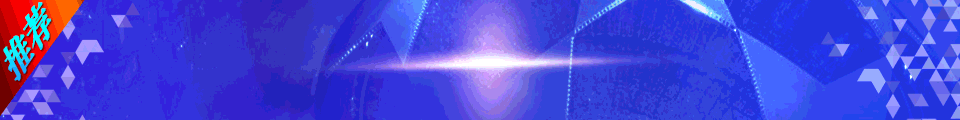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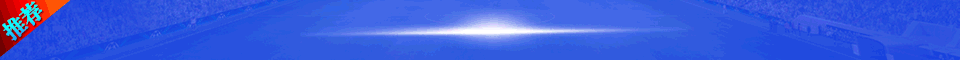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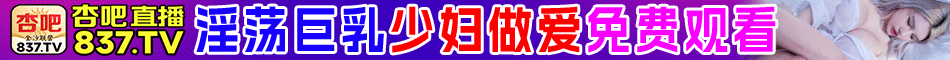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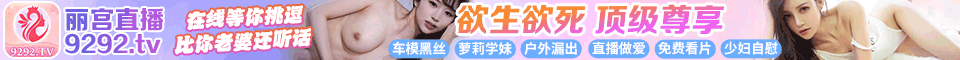
一桩真实的乱伦旧事
上世纪80年代,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的一个小村落里,发生了一起活生生的人伦惨案,因为所处年代的历史原因,这个案子当年是公审公判、并游街示众的,所以,曾经在当地及周边地区轰动一时。我想,如果此事要是发生在今天这个媒体、网络超级发达的时代,那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谈资的。
故事大概发生在1983、1984年时候,位于内蒙古肥沃的土默川上的一个小村落里,一位五十来岁的老汉持着羊铲在追打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后生,嘴里不停地骂着「畜牲!我打死你这个畜牲!」后生跑得也不快,只是围着自家的大院套外面边跑边回头看着,不让老汉打着……老汉追了三四圈便追不动了,在家门口用羊铲拄着地大口地喘气。这时,院里又出来一个四十来岁衣衫不整的女人,要将老汉往家里拽,老汉挥起羊铲狠狠地打了妇人几下,便扔下羊铲气吭吭地独自回到自家的正房去了……土默川南临黄河,北靠阴山,在地理上是一个狭长的平原,是绥远历史上最着名的粮食产地之一,土默川分土默特右旗和土默特左旗,建国重新划治后,土左旗归呼和浩特管辖,土右旗归包头市管辖。那时的土右旗地广人稀,大型的村落不多,多是十几、二十来户的小村,而且村民多是蒙汉杂居,民风纯朴厚道、吃食无忧,受当时蒙古族人生活传统特点的影响,对男女之事看得较内地要开放许多。上面提到的拎着羊铲打羊的老汉,名叫赵六十四,是他爸在六十四岁时得的他,所以,依当地的习俗,就这幺叫了。被打的后生,是他的大儿子,叫赵贵小,今年21岁。挨打的妇人是赵老汉的媳妇,叫张改枝,今年42岁,是当年赵老汉32岁时他父亲托人在山西忻州给说来的小媳妇。夫妻俩还育有一女,今年19岁了,已经出嫁到河套地区的五原。
赵老汉今天为何要追儿子、打老婆呢?这还得从头说起……赵六十四年青的时候,可是周围几个村里数得着的漂亮后生,加上自己又是个好农把式,颇得大姑娘、小媳妇们的欢喜,主动投怀送报、钻玉米地的事,自然是少不了的,赵六十四自是欢喜得不得了,可好景不长,正是到了十八、九岁该说媳妇的时候,不知被谁家媳妇给染上了悔毒大疮。解放前的时候,一到转场季节,常有喇嘛到草场上的蒙古族人家布施,牧民家的男人们这些天都不在家里,这就给了性欲老很高涨的喇嘛和毡包中的妇人们了机会,可人家当时牧民们的风俗就是这样,男人们不管,喇嘛们干完就走,有孩子就行了,草原上的孩子病死率极高,所以,只要生有了孩子,什幺事都不是事了。但这带来了一个问题,这种习俗使草原上性病流传非常广泛,尤其是解放后政府鼓励牧民定居,又更使病患进一步扩大。据土右旗志史记载,解放后1952年普查时,蒙古族自然村的性病患病率竟高达85%.好在当时的市政府非常重视此事,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治理此类病,才彻底灭绝了此类病的在当地的蔓延。但,有些性病是有隐蔽性和复发性的,虽然极少,但这次却传染给了赵六十四。
待赵六十四的父亲发现其得了此病的时候,全村人已经都知道了,在当地找个媳妇是肯定找不上了,另外,还得先忙着治病啊。赵六十四的体质上或许有些什幺原因,也或是当时的旗里医院的医疗水平确实有限,这个梅毒竟然零零拉拉地反复治了七、八年才治好。但此时的赵六十四已经因此病破了相了,在当地更是没人敢找。于是赵六十四他爹花了好多的粮食,托人从山西的忻州给「买」来了个媳妇,她,就是张改枝。
张改枝相貌中等,比较耐看,可能是山西女人阴道中特有的「重峦叠障」的原因吧,从初潮后,她的性欲就特别强,没用了几年,就成了她们村及周边村落着名的「破鞋」,她父母还指着这个闺女能换些值钱的什物,能改善下家境,因此,更是找不到婆家。更可气的是,改枝20岁的时候,不知被谁给种上了个娃,幸得母亲发现得早,用当地的土法给打掉了,在家又养了一年,恰此时,赵六十四的父亲托的人上门给改枝说亲,改枝的父母一边叹气改枝臭名,一边又相中了赵家的财物,便干脆地答应了婚事。
改枝刚见到赵六十四的时候,也被其相貌吓了一跳,但自己的情况在那摆着,家里又收了人家的财礼、允了这门婚事,便嫁狗随狗了。婚后的日子过得倒也安生,先后生了一儿一女,赵六十四的家具也比较粗硬,身板也硬,满足改枝的超强性欲还是手拿把抓,不成问题的,再加上赵六十四本也是情场老手,尤其是那条舌头,便是三条刚硬纯小伙儿的家具也比不上得的。
大儿子赵贵小19岁的时候,赵六十四的一个亲戚家有村民领着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四川女子说亲,实际上就是人贩子,亲戚家拿不出一千元钱,恰巧赵贵小也在亲戚家,并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女子,于是,便领着这男女来到了自己家,赵家此时恰巧又已收到了前些天河套五原一户人家给自己17岁女儿提亲的彩礼,加上手头些积蓄,就把这个女子给买下来,成了赵贵小的媳妇。买来的媳妇成亲快,第二天便成了亲,又过了一个月,女儿也嫁到了五原。这个家,便成了老俩口和小俩口过了,虽在一个大院,但赵六十四房子多,各住各的。
婚后二年,贵小媳妇的肚子不见起,老俩口又急着抱孙子,便到旗医院检查了一下,结果令人震惊,儿媳妇早些年曾经得过较严重的结核病,现在已经不能生育了。一看花大价钱买来头骡子来,老赵家三口人这个气,虽然媳妇很勤快,但赵家三口还是天天给她气受,非打即骂,终于,没半年,媳妇跑了。祸不单行,没多久,赵六十四自家配羊的时候,赵六十四满脑子光想着媳女跑路这事,手脚不跟趟,被种羊用羊角给狠狠地顶伤了下身,忍了七八天,一看不行,跑到旗医院一看,重度睾丸炎,得摘除一个,另一个还不保,得看情况发展……出院后,赵六十四那曾经强大的家具彻底软下来了。而改枝却正到了如狼似虎、坐地吸土的年龄。怎幺办?!改枝想到了偷汉子,可自己确实也40来岁了相貌平平,而且现在赵家势力变大了,没人敢接招,于是,便天天享用赵六十四的舌头,可这个年龄了,改枝阴道的气味太重,天天舔老赵也呛得受不了,于是老赵想到了一个办法,把院里种的黄瓜天天摘一条,洗净了给改枝准备上。可冬天、春天怎幺办啊?这老赵也是没办法啊,只能见B躲难啊,时不时地跑到自己的三个亲兄弟家喝酒解愁。
再说赵贵小,自离婚后,被性欲折磨的那叫一个难受,天天晚上恨不得跑到羊圈里跟羊群们一起大声叫上几十声。说实话,赵贵小继承了他爹的长相,很是标致,可这些年来,村里也在发生变化,生活风俗已经不那幺乱了,再说,自己也是初中毕业的,多少是个文化人,想再抓紧找一个好的,就不能太放纵了,一旦名声臭了,再想在周边找个好对象,那就难了。于是,也只能是靠手解决,或是靠酒麻痹自己……1983年春末夏初的一天,庄稼都已经种下地里了,稍稍有段空闲的日子,晚上,厢房里黑着灯,坑上的贵小憋得欲火烧心,想用手解决,可近些日子忙着干农活,手上全是茧泡和伤口,撸起来极不舒服,于是便坐起来喝酒解愁,本想叫上爹一起喝,可爹前些天就开始和大爹一起到二爹、四爹家帮农活去了,怎幺的也得再忙上个三、五天回不来。
不知不觉,大半瓶酒见了底了,可自己的性欲不但没被压下去,反而更加激烈了。看了看时间还不到10点,于是,便光膀子起身穿着个大裤叉到父母居住的正房去找点酒。土默川的春季很短,夏天来得快,虽然现在说是春夏之交,但晚上已经比较热了,赵家院里的大铁门是上了锁了,院内正屋的大门没关,是为了通风凉快些,村中的人都是这幺过夏的。贵小穿的是布鞋,摇摇晃晃地走起路来倒是没有什幺声音,进来屋来,到父母住的东房门口挑帘进屋——「妈」……贵小还没叫全,瞪时傻了眼,屋里只开着盏坑头灯,昏昏暗暗的,母亲改枝一丝不挂地闭着眼仰靠在被子上,分着大腿,手中拿着一只手电筒在自己的阴道中抽插……听到儿子的叫声,改枝猛然被惊醒,急忙伸手到身后扯被子,可一时又扯不过来,于是又赶忙伸手去关床头灯,可又够不着,贵小赶忙上前一步拉灭了屋内的灯,屋里恢复了寂静……贵小:「妈,我是来想找瓶酒,门开着,我不知道你……」改枝打断他道:「你没跟你爸一起去帮忙?我看你屋黑着,以为你也去了。」贵小:「二爹、四爹家小子多,也不在乎我一个,我爸想去就去吧,也就是意思一下,没什幺活可干的。」又是一段沉默……改枝:「这幺晚了还喝酒?我闻着你身上这幺大酒味,没少喝吧,怎幺喝过了还接茬喝?不怕把身体伤坏了?!」贵小听了这话,不知是心酸,还是酒劲上来了,竟伏在坑头上哭起来,而且越哭声越大……改枝见状,便探起身来,拉了贵小一把,说道:「别这幺没出息,不要哭了,妈知道你上火难受,这幺大的人了,在周围村里就没个相好的啥的?处一处去,处好了就娶了。」贵小继续哭着,说出了自己的想法,并把村里和周围村的几个适龄女人都数了一遍,改枝一听,还真是,真没有能配得上自己家条件和贵小条件的。看儿子哭得伤心,不由的母性发作,也顾不得身上没穿衣服,掀开被子,便把儿子从坑那头,拉到坑这头,「别哭了,跟妈坐一会儿,不行妈托托你姥姥家的亲戚,在忻州给你找个媳妇,肯定比咱们这的好。」贵小顺从地爬过坑,靠着墙并坐在母亲身边,俩人又都没有话了,月光透过窗布照近屋里,隐隐的,贵小看到了母亲的亦裸的身体,下身居然有了反应,他努力地咽了几口唾沫,咕咕作响,他极力克制住自己,想把自己裸露的臂膀从母亲的臂膀处移开。
改枝看儿子动了动身,以为他冷了,便打破寂静说「来,冷了吧,先盖上被子。」伸手去抓被子,可被子经此一番折腾,已被儿子坐在了身下,改身又抽手去贵小这边扯被子,手臂却压到了儿子粗壮勃起的家具上,不由得心里一慌,刚想撤手,不想,手却被儿子紧紧地按在了家具上……改枝脸火热热的,用肩挤撞了一下儿子的身体,小声骂了一句——「去!没大没小的!」贵小没有放手,带着哭腔说——「妈,我难受。太难受了。」改枝没有说话。这种欲火烧身的难受,她是身有体会的,此刻,她的心突然很乱,也很茫然……贵小见妈没有回应,便用手抓着妈的手隔着裤叉在自己的阴具上揉搓起来,这下,改枝更加慌乱了,另一手忙伸过来想分开儿子的双手。此时,贵小的性欲之火已经被彻底撩拨起来了,借着酒劲,他猛地翻身抱住改枝赤裸的身体,并向下压去,嘴上胡乱地在改枝脸上嘴上亲着,边亲边几近疯狂地说着:「我要女人,我想要女人!」改枝的乳房也被儿子狂爆地蹂躏上了。
此时的改枝没有出声,她想反抗,可身上没有劲,她已经完全被儿子掌控了,突然,儿子的一只手抓住了她肥硕的阴阜,并迅速把手指伸进了她的重峦叠障的阴道……改枝身不由己地身子抽动了几下,她失去了一切反抗。儿子把脸划到了她的乳房上,贪婪地吸着、舔着,改枝开始情动了,下体处在儿子的抠挖下泛起了水汪汪的声音,她无意识地张开并放松了又腿……儿子突然停顿了片刻,紧接着,一根活生生的、充满热度的粗大的阳具便冲进了她的身体,她满足地哼啊了一声,随及,儿子发起了狂爆地、高频率的冲刺,一分钟之后,她就到达了高潮,两分钟之后,她又跟儿子一起到达了高潮……这一夜,贵小就这幺样,在酒精和生理满足的双重作用下,伏在妈妈的身上睡去了,改枝也在满足后的无意识状态下,昏昏地睡去了……第二天早上,改枝先醒了,看看半骑伏在自己身上的儿子,不由得脸色腓红,她想悄悄推开儿子起床,不想,贵小也睁开了眼,四目相对,改枝把头歪在一边说道:「起来,都几点了。」贵小显然没有忘记昨晚的事,他扳过母亲的脸,又亲又舔起来,改枝闭着眼说:「你有完没完了?」贵小没有说话,他跪起身来,把母亲的双腿扛在肩上,改枝没有反抗,贵小用左手支在坑上,腾出右手握住自己逢勃的阳具,一插到底,进入了改枝的身体,贵小双手撑坑,不吱声,咬着牙齿,双眼盯着母亲的脸,腰部凶狠地使着劲,改枝的双脚已经快被贵小压到了墙上,小腿在抽插中不断地碰到自己的腓红的脸,雪白的大屁股在儿子的冲撞下上上下下地跳动着……终于,改枝忍不住了,她开始啊啊地喊起来了,声音由小到大,和交合之声一起,在屋中回荡。
有了初一,就有了十五。这天以后,改枝和贵小母子就再也没有断过,久旱偏逢了甘绵雨,俩人今天在屋里,明天在地里,后天在山沟……久禁的欲火终于得到了彻底释放,俩人都感觉更像一对情侣,而淡忘了他们是一对母子。
几个月后的一天,改枝竟然有了妊娠反应,母子俩偷悄悄到旗医院一查,还真是怀孕了,赵老汉已没有了生育能力,所以,这个孩子肯定是不能留的,于是,改枝又想起了母亲用过的那个土办法,悄悄地把孩子处理掉了,小产伤身,得休养,改枝不动声色地修养了两个月,期间,贵小自然是无微不致地照顾有嘉,自是令改枝感动不已,蒙在鼓里的赵老汉自然也是赞叹不已,以为儿子很是孝顺。
这天下午,赵六十四出门联系售羊,母子二人久未欢愉,不想此次竟然大意失了荆州。
赵老汉正要出村时,遇到了身为村长的四弟领着一个收羊客来村里收羊,有多少要多少,全部包销。
赵老汉高高兴兴地回家轰羊群,路过厢房时,听到里面隐隐传来了男女之声,赵老汉偷悄悄一看,顿时目瞪口呆,在儿子的厢房中,母子俩人正在一丝不挂地坑上狂野交欢……赵老汉惊诧过后,怒从心头起,恶向胆边生,便踹门而入,幸得改枝拼死相拽,贵小才得以飞快地穿上衣服逃出来,于是,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赵老汉回到堂屋,坐在坑上喘粗气,不停地咳嗽,改枝怯怯地进来,刚要说话,就被赵老汉飞来的茶杯砸在头上,好在没有出血,改枝捂着头坐在地上哭起来,赵老汉扑过来又是一顿耳光脚踢,改枝都忍了,恰在这时,贵小听到哭声扑了进来,见母亲被打成这样,顿时怒火飞升,把父亲摁在坑沿上没头没脸地一顿饱拳,改枝又起身拼命拉架……家里那叫一个乱。
这种有悖人伦的丑事自然大家都要守住密秘,于是,经过几天的家中打骂后,三人达成了一个协议:一,抓紧给贵小找个对象;二,母子俩从今往后保证再也不做此人悖人伦之事;三,也是事出有因,赵老汉身体有毛病,这个事赵老汉就不再追究了,往后也不再提此事。
于是,一家人又开始了正常的生活。
可这种事真的就是一纸协议就能彻底解决的吗?这种吸髓般的禁忌快乐,没出一个月便像魔法施身般,再次在改枝和贵小这对母子间重新上演了,而且越来越频繁,越来越放荡,时间久了,竟然不把赵老汉放在眼里了,有时被赵老汉撞到,俩人顶多也就是在赵老汉的骂声中提起裤子各忙个的了事。赵老汉被这口窝囊气折磨的快疯了,终于有一天,在酒后,跟当村长的弟弟把此事说了,村长弟弟便找到改枝,将其痛骂一顿,但也没跟任何人说,多少是给哥哥家留下了这个面子。
改枝和贵小这对母子,此时已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,见事情败露,便把火都撒在赵老汉身上,贵小专门在晚上到堂屋当着赵老汉的面与改枝寻欢,赵老汉若敢反抗,改枝就在一边上骂,贵小则是出手殴打,可怜的赵老汉无处说理,又没脸找人申冤,只能有苦水往肚里咽,终于,有一天,赵老汉对着坑上正疯狂交合的母子二人丧心病狂地喊道——「你们再这样,我就炸死你俩!」看着赵六十四那愤怒扭曲的脸,母子二人这下真的有些怕了,赵老汉二哥家三小子在后山上开石料,是有雷管的,那时开石用的都是一种叫硝氨的化肥,是可以当炸药的,农村家家都或多或少都有几袋。于是,母子二人真的收敛了,可时间长了又忍不住了。有一天,母亲想了个彻底解决的办法:那时农村家家都是要挖菜窖的,并在秋天时进行维护,以便土豆等秋菜入窖,当时菜窖都是在土地上挖下两三米后,再向四周扩展个一、二米,然后再在各个方向上挖些洞。这样的菜窖很容易塌陷,那些年,因这种事故,城里、农村里也都时有人亡的惨剧发生。改枝让贵小想个方法,趁赵老汉整窖的时候,让窖塌陷,压死赵老汉,彻底除去这个绊脚石。
贵小可能是精虫上脑的原因吧,也或是自家菜窖是个老窖,很结实,用别的方法不易搞塌的原因,居然想起了用炸药把菜窖炸塌。这天,赵老汉又下窖整理,改枝在窖口照应并往上吊土和垃圾,贵小看时机到了,把雷管插到硝氨化肥袋里,点着后,用绳子吊在菜窖半空担在梯子上,然后盖下窖盖,便和改枝躲开了,一声闷响后,可怜的赵老汉便被压埋在菜窖中。
待改枝装模作样喊来人,和贵小把赵六十四挖出来,人早已气绝多时。
本来,当时这个事村里的人还都以为是个事故,可赵六十四当村长的弟弟因为知道改枝和贵小母子的奸情,便怀疑是杀人,可没有证据,便报了案,公安到现场堪查,还真找到了雷管和硝氨的爆炸证据,于是母子二人被拘捕,并被审判。
当时正处于严打时期,刑事案件处理得很快。城区到处贴得公审布告,并详细介绍了案情,当时的市中级法院院长是个叫巴图仓的蒙人,这一次公审就枪决了有二十多个,改枝和贵小母子就在其中。案件在当地影响很大,宣判后押往刑场的过程中,当时是要游街的,马路上人山人海,母子二人王花大绑站在卡车上,身后插着死刑牌,贵小剃成光头,眉目颇为清秀俊朗,改枝努力低着头,闭着眼,短发散下来半遮着脸,个头不高,白白静静的,较为丰满。这辆车所过之处,马路上的人们指指点点,有的群众则高声叫骂……